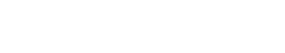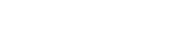信息时代的交互设计
——访中央美术学院彦风
编者按:彦风,现为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数字媒体专业讲师,毕业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装饰艺术设计专业,2003年,2007年毕业于英国伯明翰艺术设计学院绘画专业,美国旧金山艺术大学新媒体专业,分别获得硕士学位。曾任中山音乐堂,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圣之艺术空间,今日美术馆对画空间项目策划负责人。致力于UI,UE交互设计分析,跨媒体艺术实践等,作品《新大陆1.2》,《红雨》,《Summer》,《InMemory of Hutong No.28》等作品多次获得国内外奖项。日前,在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主办的“泰山学术论坛•设计艺术学专题”研讨会间隙,《中国设计》(design.gov.cn)对彦风老师进行了采访。

《中国设计》:数字媒体的发展,让广告的内容和载体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现代广告理念呈现了哪些特点?
彦风:现代的广告学已经不再作为传统媒介“广而告之”了,它以一种隐性、巧妙、娱乐性的方式存在于各种媒体当中。现代广告在理念上发生了许多变化。第一增强了广告强迫性。强迫性使广告的传播性有了很大的改善。比如用IPAD时有一个banner,你必须点击它才能进入下一关,用户是被迫的使用。以后的广告栏可能就是呈现交互式的,比如通过二维码识别,广告的视频内容就会传输到手机里,收录之后,所有的广告就可以随时随地的观看,这等于第一媒体借助二维码概念之后转化为第二媒体,大大改善和提升了广告的传播。我们可以看到北京地铁的广告中很多是用常规性的动画形式来表现的。以后我们可以把铁轨对面的广告变成带有互动娱乐性的,用手里的手机与墙上的广告进行互动,例如可以用APPS操控广告里的篮球投篮等。广告除了广而告之的作用之外,还要要让用户“主动”地去接受广告的信息,而不是被动地传递,这就是我们讲的强迫性的概念。第二是要增加广告的娱乐性。现在的生活状态压力非常大,人们需要在间断性的时候做些休闲益智类游戏。因为人都是在休闲时间来玩这些游戏,游戏本身也不需要耗费太多的脑子,这样一来就把广告与生活比较自然地衔接在了一起。除次之外还应该注重广告媒体的升级,在电视里可以对广告进行比价,比如电视正在播某种电器的广告,同时就会出现苏宁电器跟它的比对关系。我们现在所做的项目,是腾讯的“Smart TV”,它有基于LBS的比价系统,通过比对你就可以知道在离你家最近的哪个位置可以买到你最想要的那一款产品。
《中国设计》:广告的载体升级后,对以后的品牌设计会产生哪些影响?
彦风:品牌性宣传有很多,现在网络上的微博就是最大的品牌性宣传。微博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只有互粉才会使你加V程度很快,刚开始用微博的时候就要加那些有V的人,要“求粉”,粉丝多了就会有利于品牌的传播。所有的机构都开了微博,它是一个品牌的延伸和推广的手段,这也属于数字化信息传播的一种手段。为什么现在“微博”能胜过“SNS社交性网站”,因为“社交性网站”只停留在原来的一次传媒上,而微博就能加快速度。“微博”为什么有个“微”字,它一次发送的字数不能超过28个,它保证有效的信息能得到及时和更快的传播。
《中国设计》:国内外的数字媒体设计理念的发展有何差异?
彦风:国内外的数字媒体与设计理念事实上差距并不大,我们只是在软硬件的创意设计构思上有所差距。比如最好的设备都会从美国引进,因为最早的数字传媒产品都来源于美国的军工产业,60年代的时候有些淘汰性的产品被民用化或被艺术家转化为一些艺术创作的手段,比如说像“Processing”这个软件,最早的时候是提供给玩音乐的人使用的,后来数字音乐人把它做成了艺术装置以后就被大量的其他门类艺术家所接受和使用。这个软件最大的优点是模块化,不需要用特别复杂的编程语法,把感应器按模块装在上面就可以进行数字艺术的创作,对操作者的理工科背景要求很低。美国最早设置“交互”课程是在2000年左右,中央美院的数码媒体工作室是在2002年设置的这门课程,国内跟国外基本上是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只是我们在硬件方面会稍微弱于国外,但是硬件现在是可以通过很多途径买到的,所以国内外基本上是同步的。但是现在很多的艺术家和设计师的创作是为用技术而用技术,艺术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无法达到真正的统一。比如我的艺术作品已经用传统语言表达到了极致,但更多的艺术家需要它延伸出更新的点,一鸣惊人,这个时候他们就把一个数码的表现方式硬生生的套上去,然后就宣布新的作品诞生了。其实数字化技术下的艺术创作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它的概念内容和形式语言完全没贴合上。其实有些作品的艺术表达并不需要很高的技术,技术越发达,作品的话语权就越少,对它本身内容的剥离性就越强。技术只是一种工具,所以一定要善待技术,合理地加以利用。
《中国设计》:数字媒体使设计表达开始由静态视觉向动态的多媒体传播延伸,从二维平面延伸到三维立体和空间,从传统的印刷设计产品扩展到交互的虚拟信息空间,传统印刷产业的发展方向在何处?
彦风:会造成一定的冲突,但印刷是不会消亡的,印刷在许多地方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某些印刷企业,都在成立数字印刷部,但是数字印刷部成立之后,不可能所有的东西都从屏幕上看,它还是需要印刷的纸本来呈现一定信息。“纸”或“书”对人来说是有“五感”的,这种“五感”本身就是种享受,捻书页的过程就是种享受,它给了人们另外一种层面上的享受。数字化过程虽然快,但是它没有情感的积淀,在信息海量获得、快速下载、比较的同时,那种静静享受的感觉也就消失了。就像我们看《红楼梦》一样,每一个人看过书之后,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的贾宝玉形象,但是87版的电视剧出来之后,心中就有了“贾宝玉必须是欧阳奋强的形象”的概念,这样其实是禁锢了人们的思维。人们看书的过程也是人想象的过程,有很多的想象空间,但是一旦对人物形象出现了定格之后,人所想象的空间就被压缩了,所以说“读”的概念必不可少,读什麽,怎麽读,需要我们更多的呈现想像的空间而不是直接亮出结果。对网络不要产生很强的依赖性,在必要的时候要看如何去使用技术,例如美国人即使在很富足的情况下,仍然会在上车之后拿出一本书阅读,从文字当中去体会某种情感。
《中国设计》:您怎么看待当前计算机以它高效、便利、精算、大信息量等优点迅速进入设计领域的,它对设计领域产生了那些突出的影响?
彦风:数字化对当前资料的保存、编辑是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其重要性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体现在信息交互速度的加快。第二体现一个“云”的概念上,可以多平台分享。这个时代“分享”是非常重要的,数字化有利于信息的进一步传播,在数字化传播上具有很大的帮助。第三它会简化数据整理,收集的流程。第四,在编辑软件和后期制作上,数字化会大大减少制作时间与投入的精力,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产品化的创意和其他的系列步骤中去。对于数字化,在小方面讲是指个人化的工作站,使个人化设计整体部件都能够贯穿起来。从大方面上讲,跟信息安全有关系,对国家在进行管理调控,甚至在包括监控犯罪等方面都有显著的帮助。
首先,对设计领域来讲,用数字化手段来实现一些东西并不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文化背景或文化底蕴有相抵触的地方。如果数字化手段利用得好,就能够产生帮助性。以手绘为例,WACOM出了一款专门扫描的产品,你在图板上写东西的同时,它就会帮你记录并直接传输到电脑。在电脑上进行涂色和快速修改就是取自于”手绘“这个概念,大大节省了人力,也有利于创作速度的提高。
其次,数字化只是一种手段,一种媒介传播方式,是对现行问题的不完善或是信息梳理的一种有效的优化,是用来解决问题的,不应该理解成为电脑化以后手绘就行不通。当然它必然也会带来一些弊端,比如现在年轻人有了电脑以后就很少“写字”,基本都是在“敲字”,它对于文化的传播性会有所影响,写字由以前的手写习惯渐渐转变成现在一种个人爱好或是技能——如:书法艺术。应该说数字化对书法功力的表现上确实是有些许影响的,书法更多的是落到了个人或专业人群中,体现了某个特定人群的技能价值体系,不再是泛众性的。虽然最原始的东西才是最有艺术感、最淳朴、最真实的,但是数字媒介的应用这个趋势是没有办法阻挡的。如果每个人都不用电脑而去写字,这是有悖于历史发展进程的,当然我们同时需要保留我们的文化技能,二者并不完全矛盾。这就是我想表达的——数字化是大时代不可逆转的工作方法。怎么去把数字化利用好,然后再使传统文化的东西能够凸显出来,从另外一个层面再引导性地去推动,这是当下最应该解决的问题。
《中国设计》:数字时代最核心的特点是电脑和网络的广泛应用,数字媒介会给设计教育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您会觉得因为计算机、网络的存在给学生授课带来了哪些好处?
彦风:目前设计艺术院校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大部分老师的教学都只停留在使用PPT做演示方法的初级教学阶段,数字化技术的普及程度有限。如果每个院校都能够建成校园网络,那么无疑将会大大有利于现代设计教育的发展。以苹果的“Podcast”系统为例,老师在前一天把信息编排好之后发到云端,云端则会定时将这些信息发送给学生,学生每天早晨醒来之后,手机就会提醒几点上课,什麽地方去上课,GPS功能启动之后,手机上会显示出从家到学校的最近路线以及上课地点等信息。我曾经看过一个关于美国教会学校的视频演示案例,讲的是学生进入学校之后可以利用移动终端设备接收信息,因为学校所有的课程后端系统都跟移动终端设备的硬件、软件相结合,每门课都用终端来进行配合教学,再比如上学时乘坐的校车都会适时调整时间,一旦校园网收到调整时间的信息,它就会提醒你,那么你就可以临时更改路线。
因此数字技术介入教学,无疑会使教育的信息传播、资源分享等各方面更有保障和更安全。数字化对于当代的教育理念则不会产生太大影响。技术从来不是一个可怕的东西,我们需要有效的去利用它。
对于教育方面还有一个数据库的建设问题。在数字时代下,任何院校都应首先做好数据库的管理和采集工作,所有东西都编制入数据库。以某些美术院校为例,采访完专家学者们之后,很多录像带和硬盘就被扔在了某个角落里,长年累月很多采访过去之后,那个角落就会堆积大量的录像带和硬盘。这些资料只实现了一次性的传播,甚至没有机会传播,只是存档备用,而不会进行多平台的再次传播,这样的情形就等于没有有效的整理和分析数据,只是做了临时采样。如果能够建立完备的数据库系统,这些资料就可以基于云的概念、在网络上、电脑上随时被调用。在这种信息化建设方面,日本比较值得我们参考。日本的美术馆在采购纸张的时候,会根据纸张存放时产生的衰竭与生熟程度制订不同的订购计划,将十年以后用的纸、五年以后用的纸、三年以后用的纸一一分类订购,然后将这些纸通过专业管理、恒温调控置放在仓库纸架中,这样某批纸张在某一个时间段的生熟程度以及取用的最佳时间等数据就可以很精确地估计出来,最大程度上满足美术馆不同时间段不同用途的纸张需求。目前我国的美术馆还做不到这样,大多是明天要用纸了今天就去大批量采购,古画的修复过程也往往不做详细的批注和记录,这就影射出当前数据管理的缺乏和手段的单一化。
数字化管理不仅是对教育,对于整个国家文化的采集,整理、储备和记录也具有巨大的推进作用。把信息的数据化不仅能使我们的管理工作变得更加便捷,也能保证我们的子孙后代的开发和再利用,对整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设计》:交互设计与技术前沿联系紧密,作为这个专业的教师,您获取信息的渠道有哪些?
彦风:我主要是以合作课题的形式来结合学校的创作理念,企业的高端技术去做一些教学方面的尝试。企业手里掌握了大量的高新技术,如果我们不去了解,就无法在第一时间知道世界的变化,那么我也无法对学生们进行一个有效的引导。在艺术创作方面,我所追求的就是怎样将这些高新技术与我的艺术创作理念相结合,然后形成一种恰当的方式来表达我的艺术思维。
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学习,眼界的开阔是最主要的。见的事情多了就会有经验感,就像有位老师说到的“我们虽有学历,但是我们没有文化”指的就是这种“视野观”的问题。对于在校生一定要给自己一个独立的空间,要打开思路,多去其他院校,多跟不同专业的人接触,勇于尝试其他专业的东西,这样才能取长补短,比如油画专业的学生,可以试着去做建筑,然后把建筑空间的概念转换成油画的某种概念、形式、语言,或者是进行思路概念上的一种延伸,对油画产生帮助作用。
采写:张汝君